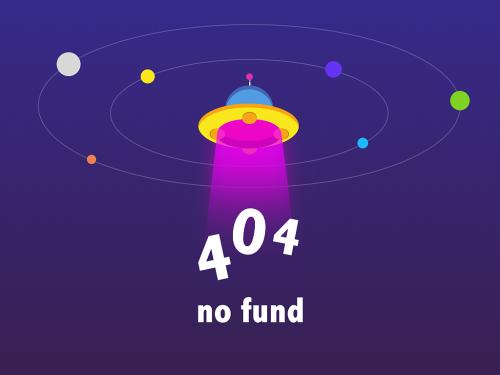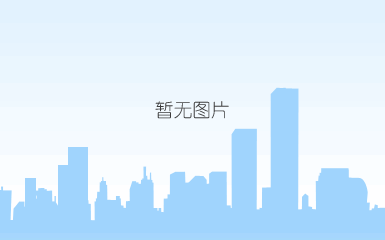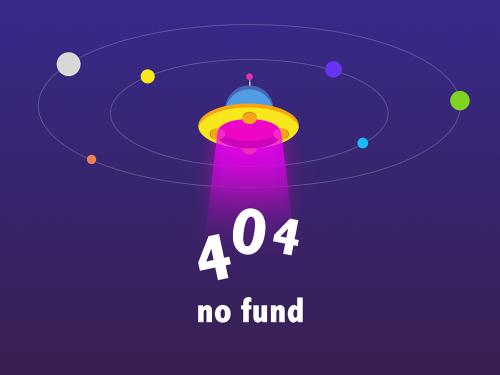在早晨,我不跟任何人交谈,我也不去想任何事情。 我尽量使自己停在一个局限的世界里。我想象我走在一个狭窄幽暗的走廊,两边是昏暗光秃秃的墙壁。我顺着走廊走下去,一直走到我能开始写作的地方。 我刷牙,穿戴好,整理好床铺。我避免跟人交谈,这一点我丈夫很清楚。我还没有进入这个世界呢,跟人交谈会引起一定的风险。昨夜已经织起一张精细的保护膜,就像鸡蛋壳里的那层膜。这层膜将我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但是它很脆弱,很容易就被刺穿弄破了。 我走过门厅进了厨房。我不喜欢早餐,可是这是必须的步骤,吃过早餐才能喝咖啡。 我弄了一碗格兰诺拉燕麦卷,沾上不含牛奶成分的替代糖浆。这两样都很甜,而且燕麦卷太干了。整个事情都很没意思,就像一碗马的饲料,但是这是必须的,而且它使咖啡更有效。 我站在厨房窗户边吃早餐。 我住在15层,窗户朝西。西边楼下面有三块褐色砂石,旁边高耸着一栋很宏伟的公寓楼。它的东墙朝向我,没有窗户,一片空白。晴朗的早晨,大概八九点之间,一片阴影出现在这片墙上,清晰而精确。这是一棵小树的影子,针叶树,浓密而繁茂,就像一颗圣诞树。真正的树本身在东边的一个屋顶花园,我从这里看不见。我永远都不会去看它的。影子树每天庄严地移动,记录着太阳的缓慢移动。在这庄严的旅程中,我注视着它完美的影子。这棵影子树在空气中安详沉静的漂浮着,而它真正的自身,在其他地方,青翠茂盛,在晨光中熠熠生辉。 我把咖啡壶通上电准备煮咖啡。是速溶咖啡。 我喝速溶咖啡因为我并不在乎它味道怎么样,我需要的只是咖啡的提神作用。我也不想等。我不想要可能会出错的机器。不想听到磨咖啡豆的吵杂的让人烦躁的声音,或是发现机器卡住了,或者其他问题。我也不喜欢看到燕麦卷吃完了。最糟糕的是发现咖啡或是加奶咖啡喝完了。我可以用土司替代燕麦卷,但是没什么可以替代咖啡,我也喝不下纯咖啡,因此我很注意从来不会等到它们喝完。 我不读报或听新闻。只要扫一眼新闻标题,扫一眼世界上可怕的苦难,保护膜就会会被刺穿,枯萎变成潮湿的碎片。我将被推入外部世界,要求对不忠的政治家、动荡危险的中东,全球变暖的威胁发表看法,我真的应该采取行动。外部世界的呼声急迫而严苛。 所以我不读报或听广播。我也从来不打电话,甚至不会打电话询问管道工能不能来修理水槽,就算他说好了要过来而现在已经过去五天了。打一个电话就会让我疲惫不堪。进入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事都很复杂,要求你做决定,要求你跟人交流,这意味着一切的结束。这意味着永远都没法定下来开始写作了。 早晨如此重要的原因是晚上我在另外一个地方,不在这里。 这个地方我无法向你描绘出来,因为它是神秘而无限的,是一个人思维所能到达的地方。深沉,缓慢的洋流,远在表面之下,以不需要我理解的方式推动着我。那里没有声音,没人监视。早晨醒来,我仍然沉浸在那个无声的前意识的模糊不清的状态,仍然沉浸在自己内心。我还在那个深远寂静的地方,听着那里的声音,跟这个外部世界的声音是多么不同。 咖啡壶发出尖锐的啸声。我把沸水倒进杯子,晃一圈,再倒出来。咖啡一定要很烫。我把咖啡倒进加热过的杯子,然后把沸水倒进去。咖啡融化了,杯子里是黑色的液体。我相信这是想象力的万能药。没有它我就没法写作。我坚信这一点。我加进去一大块咖啡伴侣,黑色就变成泛着奶油的浅褐色。 在我的书房里,我绕过书桌走过房间把咖啡杯摆在写作椅子旁。电脑在桌上,一截短的蓝色电缆连着网络。我拔去网线,把笔记本电脑搬到我的写作椅,这里网线够不到。我坐下来,摆脱了网络上没完没了的信息干扰。我的电脑现在没有任何人的观点或意见,只有我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我会读会儿书,进入一种对我写作有帮助的情绪感觉中。写作《我女儿》(this is my daughter)时我会读《约翰·契佛日记》(the journals of john cheever)。写《甜水》(sweetwater)时我会读《安娜·卡列尼娜》。写《代价》(cost)时我会读《时时刻刻》(the hours)。写《斯巴达》(sparta)时我会读《赎罪》(atonement)。我对那些书很熟悉。我可以随便翻开其中一本也知道那一段写的什么。我把《赎罪》的书脊都弄坏了,尽管我只读其中的一章,翻了一遍又一遍。 我只读一两页,然后就把书合上。 就是这个时刻。在一个好天气里,我呆在我该在的地方,仍然在那个深深的梦一样的地方,而我还可以聆听。 此时此刻,我就像是那棵树。 在美好的一天,我被一些比我自身更重要的事情所控制,沐浴在天堂洒下来的光之中。只要短暂的被照耀充电,我就可以投射出我想象出的事物的影子。这个影子绝不是我所知道的存在于某处的明亮的真正的实物,但是我会尽可能使它精确、真实、强烈、美丽。我要把这影子投向天空,在那里它永远也不会被看到,或者可以远远地被看见,而且是只被某一个人看到,这个人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是谁。重点是要把影子投到天空中去。 我开始了,在键盘上轻轻敲击,确定词语,希望那光能把我照耀。 |
我是如何开始写作的 -j9九游会官方
2014-04-10 12:45:41 来源:阅读之美 点击:
下一篇:去月亮上扫星星
相关阅读:
- 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有多煎熬 (2014-04-28)
- 你遇到的那点痛,算什么(2014-05-06)
- (2014-05-21)
- (2014-05-21)
- (2014-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