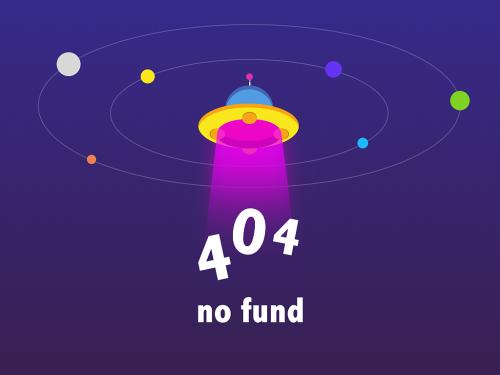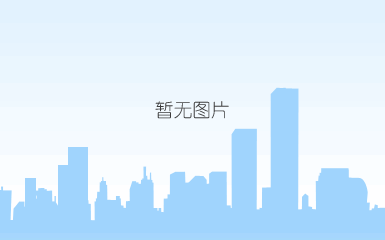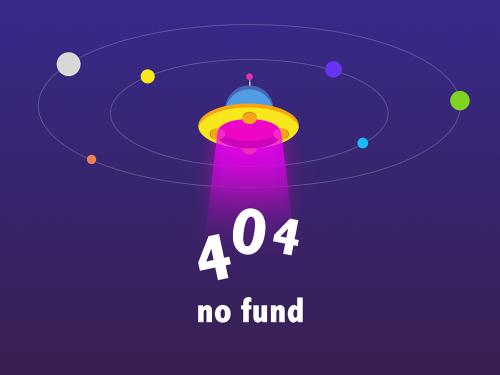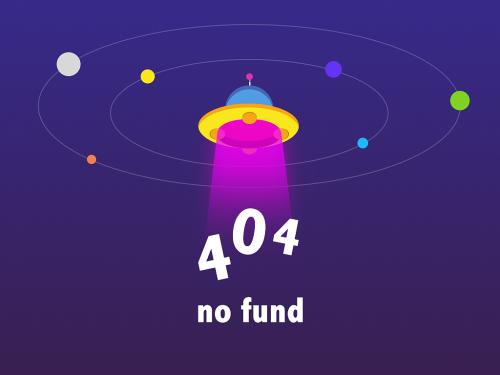 奥卡万戈三角洲的一对白犀牛 在肯尼亚中部,世界上仅存的四只北非白犀牛中有三只生活在这里,而它们却固执地拒绝繁殖。从2009年开始,保育工作者就尝试将这几只犀牛“笼络”在一起,结局却以失败告终。如今,唯一的一头雄性北白犀已经接近43岁,年事已高无法生育,这一白犀亚种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市,科学家正在试图复苏它们的种群。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再生药物研究者珍妮·洛林(jeanne loring)已经找到了从犀牛皮肤上获得多潜能干细胞——能发育成任何类型的细胞——的方法。她和同事们正在研究如何将这种干细胞培养成犀牛的卵细胞和精细胞。如果获得成功,他们就有机会通过试管内授精培养出新的犀牛个体,从而将这一亚种从灭绝的边缘拯救出来。 北白犀并非唯一接近人工复苏的物种。对于那些已经完全灭绝的物种,科学家只能借助于保存在低温储藏库(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冷藏中心)里的动物细胞和植物细胞。还有的研究者采用人为杂交的方法,将濒临灭绝的物种与另一相似的物种进行杂交,从而保存该物种的一部分特征。 通过这些方法,生物学家可能很快就能将灭绝物种重新带回我们的视线之内。这是很激动人心的进展,但的确是一种不自然的保护自然的方式。一些科学家和保育工作者也提出了疑问,复活灭绝动物是否能真正地保护地球的濒危物种? 没有野性的荒野 许多关于复活灭绝物种的争论其实已经重复了很长时间,几十年来,保育工作者和科学家在使用更为传统的方法时,也一直面临着同样的反对意见。当拯救某一物种的成本过于高昂——比如拯救非洲胎生蟾蜍需要数千万美元——的时候,有人就会提出自然选择的力量是人类不能违背的。如果一种动物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那它就应当被淘汰。对一些自认为是“绝对达尔文主义者”的科学家来说,这种逻辑同样适用于那些被人类逼得走投无路的物种,如白犀牛和平塔岛象龟等。“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这一逻辑也适用,耶鲁大学的科学史学家乔安娜·雷丁(joanna radin)说,“所以,这就是适者生存。” 如果科学家选择拯救一个物种,这并不意味着该物种就能繁盛起来。例如,当保育工作者将曾经濒危的美洲鹤放归野外时,如果没有人类飞行员驾驶飞机进行引导,这些鸟儿已经无法进行迁徙。如果珍妮·洛林成功地繁殖出北非白犀牛,她也无法将其放回野外——偷猎者会杀死它们。“除非我们能在地球上为其他物种留出空间,否则复活多少动物都是徒劳的,”m.r。 奥康纳(m.r。 o’connor)在她的《复活的科学》(resurrection science)一书中写道,“地球上留给它们的空间已经不多了。” 那么,这些复活的动物会在哪里生存呢?动物园。珍妮·洛林将自己的工作形容为“没有恐怖情节的侏罗纪公园”,这部分是因为她的新实验最终可能只是成为一个活的博物馆。如果动物无法在野外生存,那保留它们是否还有意义呢?一位环境伦理学者说:“一只动物园里的老虎已经不是真正的老虎,因为它无法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珍妮·洛林也意识到,复活出一只被剥夺了自然家园的动物很难称得上是理想的j9九游会官方的解决方案。“我不希望拯救一种只能继续存在于动物园里的动物,”她说,“但这可能比什么都没有强。” 对物种消失的担忧正是科学家将濒危动物的细胞保存起来的原因,这相当于建立一个“原初动物园”(圣地亚哥市的一个机构自称为“冰冻动物园”)。这些“dna银行”被当作保险柜来使用,科学家对保存起来的样品——从喜马拉雅山脉的云豹到大堡礁的珊瑚——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从某种意义上,把动物冷藏起来是一种让步,表明我们还不确定如何拯救它们,”奥康纳写道。 在动物灭绝之后,这些保存下来的细胞将如何处理,目前还存在争论。如果正如珍妮·洛林对白犀牛的尝试那样,诱导干细胞转化为精子和卵子,那科学家就能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新的动物。或者,他们还可以尝试将灭绝动物的特定dna转入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现生物种中(一位科学家希望对大象细胞进行类似的尝试,从而复活猛犸象)。 不过,如果我们一心专注于保存dna,可能会事实上导致动物真正的灵性消亡。奥康纳指出:“没有人会认为保存起来的人类dna能保留住使我们成为人的东西。”举例来说,为了复活已灭绝的加拉帕戈斯象龟平塔岛亚种,科学家尝试将一些具有部分该亚种dna的其他象龟进行近亲繁殖,这个过程已经进行了有一个世纪,其中一只后代可能具有所有平塔岛象龟的dna。这只象龟是否就是曾经的那种象龟,相信许多人都有不同意见。“说起来有点矛盾,”奥康纳说,“我们介入得越多,想要拯救物种,它们的野性往往会变得越来越少。” 人类的自责 或许人类在道德上具有拯救一些灭绝物种的义务。对珍妮·洛林来说,白犀牛是复活的良好候选者,不仅是因为它们是非洲大型野兽的重要象征,而且因为它们灭绝的原因。“犀牛之所以走向灭绝,源于一个非常直接的过程——人们杀死它们以获取犀角,”洛林说,“我认为我们有责任去拯救这些动物,它们是被我们杀死在野外环境中的。” 不过,拯救白犀牛的尝试可能还有另一个动力:人类的私心。50年前,科学家成功地克隆出鲤鱼,现在是一个易危物种。不过,利用这一技术使鲤鱼的数量回升,听起来并不如把白犀牛从灭绝边缘拯救出来那么有吸引力。据估计,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地球物种灭绝速度比自然状态下的速率快了100倍。然而,只有那些在人们心中获得喜爱——或者让人觉得特别有罪恶感——的物种才能获得拯救的机会。“我不会拯救蚊子,”洛林说,“相信我。” 如此说来,拯救灭绝物种更多的只是一个自我满足的动物保育标签。复活灭绝动物表明我们迫切地需要有所行动,但这是为了人类,而不是为了动物。对已经灭绝的动物来说,它们是否复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任天) |
灭绝物种是否应该复活?或导致动物野性尽失 -j9九游会官方
2015-11-16 09:11:11 来源:新浪科技 点击:
下一篇:地球会不会变成下一个火星?磁场被削弱但仍坚挺
相关阅读:
- 科普阅读:星系肥胖或扁平取决于转速(2014-04-09)
- 科学现象:植物为何可以导电(2014-04-09)
- 科学探究:空气的质量(2014-04-09)
- 现代农业的三种成功模式(2014-04-11)
- 浓硫酸和稀硫酸的鉴别方法(2014-04-11)